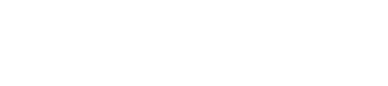【吳鴻昌老師紀念文集】緬懷鴻昌學長—一位學術的先行者與我的人生導師
2020-03-03
文/劉惠純(台大農服、台大社會學研究所 R91 級)
在台大農服社團裡,不管學弟妹或學長姐,大家都直呼鴻昌學長—老昌,在台大社會系,學弟妹則親切地喊他—大毛學長。掐指算算,我認識學長已超過20年,當年我先是跟學長在農服這個大家庭裡相遇、相識,學長大我三屆,是社團其他學長姐口中「愛談理念」的傳奇人物。第一次上學長的社課,學長運用了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解釋為什麼服務理念是重要的。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說人在追求溫飽之後,會有追求自我價值的更高層次需求,而大學生之所以要下鄉服務,是身為考試體制下的受益者對這社會應有具體認識與實踐改變的責任。當時在台大校園裡,大部分人的社團首選是服務型社團,我也是追隨這股大潮下鄉去,但在學長的社課中,我頭一次知道,「服務別人也是要有理念的,不是一片善心人家就得接受」,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發展研究中不能迴避的倫理命題,小大一的我,只是默默地崇拜口才便給、順手捻來即是經典的知識型網紅(雖然當時並沒有網紅這個詞彙),在法律系深受解釋學演繹層次之苦的我,受學長鼓勵,從大二開始旁聽社會系的課,如同開啟知識上的另一道大門,社會學的百花齊放、學派間萬家爭鳴,是讓我決定從法律系放手的主因。最後我決定研究所也追隨學長的腳步,考進了社會所。學長可說是啟迪我社會學之路的重要推手。
不管是老昌或大毛學長,有學長在的地方,總是熱熱鬧鬧,社會系的學弟妹來到知名景點—後門講堂,川流不息地拜碼頭,熱心健談的學長專治各種疑難雜症,從課堂報告、考研、田野、博碩士論文、謀職、從戀愛怎麼起頭到不愛如何放手,問事者眾,他們帶著困惑而來,最後大多能笑著離開,學長當年沒有擺攤向問事信徒收費,真的是很吃虧;也有社團上下屆之間的八卦流轉,大我一兩屆的學長總是笑著說,老昌啊就是那個冬天裡永遠穿著一襲黑色大衣,手裡叼根菸,眉頭深鎖地拿著幾本有字天書,從化工系改念社會所的聽起來很酷的一個人,還沒親炙學長本人風采,就耳聞學長當年在農服營隊擔任值星,冷酷嚴峻的表情不知嚇著多少出隊的學弟妹,但實際上是個面惡心善的大好人。
刀子嘴豆腐心,外冷內熱;看似風流倜儻,其實專一不二,關於學長的傳說總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同時身為社團學妹跟研究所學妹,我總覺得自己對學長更多了一分親密感,學長不只是令人仰之彌高、循循善誘的學術先行者,而是哥哥與人生導師。每當我在人生的低谷時,第一個浮上腦海的念頭總是:不如找學長談一談吧。在我大二向父母表達,我對法律沒有興趣,將來也不想考律師、司法官時,掀起一場風暴,學長知道這件事後,好言相勸,勸我在態度上,不用這麼劍拔弩張,也不需急著轉系,可以先把法律系的大學學位完成,因為這是相對在就業市場上好找工作的科系,所以最後我跟父母達成共識,在拿到法律系的大學學位後,到研究所再去念自己喜歡的社會學。
這件事讓我知道,學長總是在追求理想的夾縫中,彎彎巧巧試圖達到多方平衡,他是個浪漫的務實主義者。談起知識,也不限於社會學上的書本知識,不管是文學、哲學、經濟學、歷史等,學長求真時,眼神是發亮的,對知識有的只是一股純粹的赤誠,而不是能夠兌現成多少真金白銀的文化資本,是馬斯洛心理需求最高層次的展現;但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現實生活時,學長則知道不能只有風花雪月,自己對打造生活安全感有份責任。
學長熱愛自由、敢於問大問題的個性,也反映了在他的學術軌跡上,不急著將知識快速變現的選擇。他的碩班論文以概念史的取徑對人民主權進行系譜學的考察,這是一本非常立基於「西方」觀點的碩論,關切西方現代性的內生價值如何與西方思想傳統下的共和主義交融,因理念的親近性而出現法西斯主義這樣的悲劇。他的博班論文則是跳轉到經濟社會學領域,一樣是從思想史著手,探問去歷史、去社會的「市場觀念」是如何成為經濟學本體論的預設。學長所鑿開的知識切面,都是大哉問,在側重本土化個案或比較性經驗研究為主流的當代社會學學界,這樣的知識企圖與視野是很難得的,也是一條較為困難的道路,學長獨身探索,在知識路上踽踽獨行,憑藉著他對知識的好奇與品味,凝視我們繼受的西方知識體系,這一兩百年來是怎麼進行漫長的演化,變成今日的面貌。分析這些知識紋理格外需要基本功,十年磨一劍,還可能成果有去無回。但學長就是這麼執著,又有信心自己能夠做到的人。
談及這些,說我對學長後來的學術際遇不可惜是騙人的。
在我大學高年級開始,台大進行了課程改革,開設了服務學程學分。但弔詭的是大學生志願參加服務性社團的人數卻雪崩式地下滑。服務型社團接連倒社,我待過的農服,當年號稱台大第一大社,一年能夠收近一兩百位新生的老社團,再也得不到新世代的青睞,在我念研究所第二年時,應聲而倒。這或許反映了我們時代的危機,對於學生學習的行政控制過多,犧牲了由下而上自由衝撞出的自主性。我們這一世代面對的學術環境亦復如此,官僚體制追求的治理理性與講究績效的管理主義,讓學長這樣非典型的學者,只能游離在體制的縫隙之間。但學長對於自己的遭遇,卻少有怨恨,他總是一如往常,一見面就關心我的近況,知道我到英國唸書後,也常常在我做田野返台休假的期間,不斷跟我討論中國研究的有哪些有趣的研究發現。
就如同他是個浪漫的務實主義者一樣,他這一生給我們這些遭遇到人生挫敗的學弟妹的解方都是一樣的,誠實認識到自己面對的問題、心寬氣和,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在我得知他罹癌的第一時間,我在倫敦地鐵上哭到不能自己,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好的人會得了這麼嚴重的病。但是我事後得知,他當時已積極地介入他的疾病治療方式,大量閱讀醫學文獻與醫生討論治療方式,也與我們這些相熟的學弟妹分享病況。
社會學慣常談大於個人的結構、談社會實在、談集體性,都是要讓我們學會看見那些加諸於我們身上的敘事框架乃至結構限制,是如何創造出異質且分化的我們,但我們是否能夠真的跳出自己的生命框框,而非宿命地認為沒有選擇,甚至憤世嫉俗,這些卻因每個人的修為而有很大差異。社會學也很少教我們面對死亡,面對未知的世界。學海無涯,知識無涯,但人的生命長度卻是有限的,人的存在是否也是呢?
這回社會學沒教的事情,我從學長身上看到,在他罹癌之後他用著極其不便的肉身,積極正向地面對生命的難關,雖然很不幸地,學長這次沒有闖關成功。但在學長的治療過程中,我卻很少看到他頹喪與悲觀,甚至我們比以前更常在臉書上聊天,學長說他有陣子因為疼痛不太好睡,我們就聊聊政治。現代醫學的進步讓大多數罹癌者頻繁進出醫院,見證自己從腐朽到死亡的終點漫長而孤寂,學長尚未走到那一步的開端,就已驟然離開,對於活著的我輩而言,這其實是很難消化的事實,但學長這一生,卻給了我們眾人許多難以言喻的溫暖與愛,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週也不例外。看著臉書的悼念文,很多人都提到因為台灣的疫情升溫,學長經常在臉書私訊問起友人最近需不需要口罩,可以去找他拿,我也不例外。因為要跟學長約拿口罩,在回英國前一天我們彼此約定好地點,我當時並不知道那就是最後一面,就像往常一樣,我們總是聊到超時。聊到咖啡店打烊、餐廳關門了,移師到街邊我們還是繼續有說有笑。學長總是有始有終,生命大敵當前,還是不畏難地當個舉重若輕的勇者,罹癌後學長有天在臉書跟我說,「我竟然變胖了,從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來是個癌末患者。」我想這就是學長與眾不同之處,你走過的路怎麼不可以留下驚嘆號呢。
學長在他有限但盛放的生命裡走過一回,讓我認知到,人並非孤島一般的存在。你走過的路,那些愛的力量就像一個很長的鏈條一樣,聯繫起不同人間的生命,這些影響會傳承下去,既久且長。就像我們當年在農服,每屆學長姐學弟妹都會讀的一本童書「失落的一角」一樣,我們各自帶著我們的缺陷去追尋人生的意義,我們一直在找遺失的美好,但其實尋找的過程足以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的美好,儘管路程顛仆。學長的一生對學弟妹、對同學者、無私而熱情地分享,是最好的教育者,已功德圓滿,身處疫病蔓延的2020年,祝福學長到了一個更好的遠方。雖有遺憾,但有的是更綿長的思念與對你的愛永存。不敢說學習你的精神,因為你好學的精神,我不及萬一,只希望能學習到你的大器與豁達,一路好走。
在台大農服社團裡,不管學弟妹或學長姐,大家都直呼鴻昌學長—老昌,在台大社會系,學弟妹則親切地喊他—大毛學長。掐指算算,我認識學長已超過20年,當年我先是跟學長在農服這個大家庭裡相遇、相識,學長大我三屆,是社團其他學長姐口中「愛談理念」的傳奇人物。第一次上學長的社課,學長運用了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解釋為什麼服務理念是重要的。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說人在追求溫飽之後,會有追求自我價值的更高層次需求,而大學生之所以要下鄉服務,是身為考試體制下的受益者對這社會應有具體認識與實踐改變的責任。當時在台大校園裡,大部分人的社團首選是服務型社團,我也是追隨這股大潮下鄉去,但在學長的社課中,我頭一次知道,「服務別人也是要有理念的,不是一片善心人家就得接受」,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發展研究中不能迴避的倫理命題,小大一的我,只是默默地崇拜口才便給、順手捻來即是經典的知識型網紅(雖然當時並沒有網紅這個詞彙),在法律系深受解釋學演繹層次之苦的我,受學長鼓勵,從大二開始旁聽社會系的課,如同開啟知識上的另一道大門,社會學的百花齊放、學派間萬家爭鳴,是讓我決定從法律系放手的主因。最後我決定研究所也追隨學長的腳步,考進了社會所。學長可說是啟迪我社會學之路的重要推手。
不管是老昌或大毛學長,有學長在的地方,總是熱熱鬧鬧,社會系的學弟妹來到知名景點—後門講堂,川流不息地拜碼頭,熱心健談的學長專治各種疑難雜症,從課堂報告、考研、田野、博碩士論文、謀職、從戀愛怎麼起頭到不愛如何放手,問事者眾,他們帶著困惑而來,最後大多能笑著離開,學長當年沒有擺攤向問事信徒收費,真的是很吃虧;也有社團上下屆之間的八卦流轉,大我一兩屆的學長總是笑著說,老昌啊就是那個冬天裡永遠穿著一襲黑色大衣,手裡叼根菸,眉頭深鎖地拿著幾本有字天書,從化工系改念社會所的聽起來很酷的一個人,還沒親炙學長本人風采,就耳聞學長當年在農服營隊擔任值星,冷酷嚴峻的表情不知嚇著多少出隊的學弟妹,但實際上是個面惡心善的大好人。
刀子嘴豆腐心,外冷內熱;看似風流倜儻,其實專一不二,關於學長的傳說總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同時身為社團學妹跟研究所學妹,我總覺得自己對學長更多了一分親密感,學長不只是令人仰之彌高、循循善誘的學術先行者,而是哥哥與人生導師。每當我在人生的低谷時,第一個浮上腦海的念頭總是:不如找學長談一談吧。在我大二向父母表達,我對法律沒有興趣,將來也不想考律師、司法官時,掀起一場風暴,學長知道這件事後,好言相勸,勸我在態度上,不用這麼劍拔弩張,也不需急著轉系,可以先把法律系的大學學位完成,因為這是相對在就業市場上好找工作的科系,所以最後我跟父母達成共識,在拿到法律系的大學學位後,到研究所再去念自己喜歡的社會學。
這件事讓我知道,學長總是在追求理想的夾縫中,彎彎巧巧試圖達到多方平衡,他是個浪漫的務實主義者。談起知識,也不限於社會學上的書本知識,不管是文學、哲學、經濟學、歷史等,學長求真時,眼神是發亮的,對知識有的只是一股純粹的赤誠,而不是能夠兌現成多少真金白銀的文化資本,是馬斯洛心理需求最高層次的展現;但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現實生活時,學長則知道不能只有風花雪月,自己對打造生活安全感有份責任。
學長熱愛自由、敢於問大問題的個性,也反映了在他的學術軌跡上,不急著將知識快速變現的選擇。他的碩班論文以概念史的取徑對人民主權進行系譜學的考察,這是一本非常立基於「西方」觀點的碩論,關切西方現代性的內生價值如何與西方思想傳統下的共和主義交融,因理念的親近性而出現法西斯主義這樣的悲劇。他的博班論文則是跳轉到經濟社會學領域,一樣是從思想史著手,探問去歷史、去社會的「市場觀念」是如何成為經濟學本體論的預設。學長所鑿開的知識切面,都是大哉問,在側重本土化個案或比較性經驗研究為主流的當代社會學學界,這樣的知識企圖與視野是很難得的,也是一條較為困難的道路,學長獨身探索,在知識路上踽踽獨行,憑藉著他對知識的好奇與品味,凝視我們繼受的西方知識體系,這一兩百年來是怎麼進行漫長的演化,變成今日的面貌。分析這些知識紋理格外需要基本功,十年磨一劍,還可能成果有去無回。但學長就是這麼執著,又有信心自己能夠做到的人。
談及這些,說我對學長後來的學術際遇不可惜是騙人的。
在我大學高年級開始,台大進行了課程改革,開設了服務學程學分。但弔詭的是大學生志願參加服務性社團的人數卻雪崩式地下滑。服務型社團接連倒社,我待過的農服,當年號稱台大第一大社,一年能夠收近一兩百位新生的老社團,再也得不到新世代的青睞,在我念研究所第二年時,應聲而倒。這或許反映了我們時代的危機,對於學生學習的行政控制過多,犧牲了由下而上自由衝撞出的自主性。我們這一世代面對的學術環境亦復如此,官僚體制追求的治理理性與講究績效的管理主義,讓學長這樣非典型的學者,只能游離在體制的縫隙之間。但學長對於自己的遭遇,卻少有怨恨,他總是一如往常,一見面就關心我的近況,知道我到英國唸書後,也常常在我做田野返台休假的期間,不斷跟我討論中國研究的有哪些有趣的研究發現。
就如同他是個浪漫的務實主義者一樣,他這一生給我們這些遭遇到人生挫敗的學弟妹的解方都是一樣的,誠實認識到自己面對的問題、心寬氣和,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在我得知他罹癌的第一時間,我在倫敦地鐵上哭到不能自己,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好的人會得了這麼嚴重的病。但是我事後得知,他當時已積極地介入他的疾病治療方式,大量閱讀醫學文獻與醫生討論治療方式,也與我們這些相熟的學弟妹分享病況。
社會學慣常談大於個人的結構、談社會實在、談集體性,都是要讓我們學會看見那些加諸於我們身上的敘事框架乃至結構限制,是如何創造出異質且分化的我們,但我們是否能夠真的跳出自己的生命框框,而非宿命地認為沒有選擇,甚至憤世嫉俗,這些卻因每個人的修為而有很大差異。社會學也很少教我們面對死亡,面對未知的世界。學海無涯,知識無涯,但人的生命長度卻是有限的,人的存在是否也是呢?
這回社會學沒教的事情,我從學長身上看到,在他罹癌之後他用著極其不便的肉身,積極正向地面對生命的難關,雖然很不幸地,學長這次沒有闖關成功。但在學長的治療過程中,我卻很少看到他頹喪與悲觀,甚至我們比以前更常在臉書上聊天,學長說他有陣子因為疼痛不太好睡,我們就聊聊政治。現代醫學的進步讓大多數罹癌者頻繁進出醫院,見證自己從腐朽到死亡的終點漫長而孤寂,學長尚未走到那一步的開端,就已驟然離開,對於活著的我輩而言,這其實是很難消化的事實,但學長這一生,卻給了我們眾人許多難以言喻的溫暖與愛,即使在生命的最後一週也不例外。看著臉書的悼念文,很多人都提到因為台灣的疫情升溫,學長經常在臉書私訊問起友人最近需不需要口罩,可以去找他拿,我也不例外。因為要跟學長約拿口罩,在回英國前一天我們彼此約定好地點,我當時並不知道那就是最後一面,就像往常一樣,我們總是聊到超時。聊到咖啡店打烊、餐廳關門了,移師到街邊我們還是繼續有說有笑。學長總是有始有終,生命大敵當前,還是不畏難地當個舉重若輕的勇者,罹癌後學長有天在臉書跟我說,「我竟然變胖了,從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來是個癌末患者。」我想這就是學長與眾不同之處,你走過的路怎麼不可以留下驚嘆號呢。
學長在他有限但盛放的生命裡走過一回,讓我認知到,人並非孤島一般的存在。你走過的路,那些愛的力量就像一個很長的鏈條一樣,聯繫起不同人間的生命,這些影響會傳承下去,既久且長。就像我們當年在農服,每屆學長姐學弟妹都會讀的一本童書「失落的一角」一樣,我們各自帶著我們的缺陷去追尋人生的意義,我們一直在找遺失的美好,但其實尋找的過程足以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的美好,儘管路程顛仆。學長的一生對學弟妹、對同學者、無私而熱情地分享,是最好的教育者,已功德圓滿,身處疫病蔓延的2020年,祝福學長到了一個更好的遠方。雖有遺憾,但有的是更綿長的思念與對你的愛永存。不敢說學習你的精神,因為你好學的精神,我不及萬一,只希望能學習到你的大器與豁達,一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