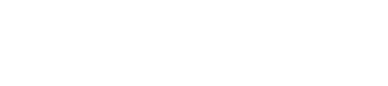【吳鴻昌老師紀念文集】紀念一位難得的學長,我們在社會學的路上曾經那麼開懷地聊天
2020-03-02
文/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我大約是在2000年準備考研究所的那時開始認識鴻昌學長,之後因為我們都有著長時間待在系館研究室的生活型態,到2010年畢業為止,幾乎是很常見面。鴻昌是個很溫暖的人,對人的真誠不會因為你是(遜遜的)學生或是(知名的)學者,而有很大的落差,如果談論的話題跟知識有關的話,更是如此。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特質真的是很難得。
跟學長聊天談論社會學相關的東西(我不會想硬說這一定是在聊學術),總是有一種讓人很想繼續聊下去的感覺。碩士班畢業以前不太知道為什麼,到了博士班中後期,漸漸體會其中緣故。我想,或許跟他(從化工系)到社會系之前,已經修過許多社科院其他系(例如:經濟、政治、法律)的課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說,他很能跟我聊法律學與社會學之間的差別,這實在是很難得的事,特別是關於知識本身的內在特性,與浸淫(或熱愛)其中者所養成的性格形塑,或者是兩者之間的相互構成。有時候我們也會像玩角色扮演一樣,從法律學跳到經濟學跳到社會學,來討論對同一個事情的不同觀點與其展現,甚至是彼此之間的知識攻防。其中深刻處有嚴肅也有輕鬆,但並非戲謔如網路上流傳的那種N x M的偏見格子、一句話惹怒OO系、或者學科鄙視鏈等等。
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佩服他的地方,或許是他在綜合比較過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觀點之後,才選擇了社會學這條道路的緣故。不像我(或大多數人)有時很難區別自己是否出於逃避其他,才轉而把社會學視為一根浮木,為了求生或秀異而緊緊抓住,卻事後貼上「一見鍾情」的標籤。他這種令人佩服的地方我當時不知道怎麼描述,後來看到一些比較炫的口號(例如「跨領域」或「科際整合」之類的東西)才瞭解大概可以這樣說。閱讀相關學科的知識,以此持續反思與社會學結緣的初衷,在很多人看來只是他的一種個人興趣。隨著歲月成為人生的沉重負擔,我才漸漸發現,這看似個人的事卻決定了一個社會學博士,能否坦然樂觀地面對殘酷現實的學術市場,甚至面對自己與社會學的關係。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廣博涉獵,一直都是他對知識保持好奇心的動力,讓他溫暖且恆續的光源,照亮像我這樣(有時虛無隨波或是自暴自棄)的人。
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的場景,是跟他在系館後門的販賣機附近,討論自己碩士論文初稿的一章又一章。他總能釐清我很多攪在一團的想法、刺激我想出新東西,甚至也能讀出偽裝艱澀文字背後我的自信不足。在研究所的學習過程中,我漸漸對這樣的關係上癮,喜歡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我的觀察、我讀了什麼書、寫了什麼報告。但我不會用「老師」來形容他,可能是這個符號已經被另外一類關係所佔據,兩者明顯不同。跟他有過比較深刻互動的學弟妹或許能瞭解我的意思。一時間我還找不到合適的文字去描述,但「學長」一詞只能扮演一個方便卻不精準的代號。因為他改寫了這兩個字過去給人的那種權威、恣意的性質,當然,「理論」、「歷史」、「讀書會」等詞彙也是。
在系館將近十年的朝夕相處中,我認識的鴻昌雖然樂觀,卻不是那種天真或有各種「不務實」症狀的人,更不會因為是以社會理論作為知識興趣,而對自己境遇或對外在環境產生過度烏托邦的幻想。與此相反,現實生活中的細細瑣瑣常常牽絆著他。
首先就是錢。他一直都在當課程助教與研究助理,但有意思的是,這既支撐了生活所需,也使其脫離了生活所需之累。拼湊幾個兼職工作的薪資以到足夠支撐生活開銷,但是,他卻把這些「工作」做到了一種「高於貨幣所得」的奇特境界。或許有人會笑他花太多時間(相對於薪資)在這些事上,他卻覺得自己已經提前攤還了許多未來要付出的「代價」。這種意義上的助學貸款我自己在剛教書的前幾年償還得很辛苦。在樂此不疲的同時,這些事竟然也從工作變成娛樂,達到開源之外的「節流」功能。我不覺得他在其中有任何的禁欲主義成分,也不相信他被困在自我剝削的虛假意識之中,但他確實使那些「為了生活所需」之事,成為幫自己脫離生活所需之累的助力。還記得當年面對後輩學弟妹對此問題的疑惑,他總是開開玩笑地說:「這是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喔!」我則在旁邊淺笑,心中OS:要學大概也很難吧?
再來是人情。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某種超乎禮物交換或人脈累積的「無所為而為」邏輯。一般來說,人際關係如果沒有利益或情愫在其中流動,很難長時間維持。可在鴻昌身上,我看到的多管閒事或好為人師(他自己的用語),似乎卻多了一種知識上的好奇。除了遙遠的人事物,我們也曾談論學生或老師,但是,他的好奇是一種具有同理心的長期觀察(也有時候被笑是種「溫情」),而非止於冷靜的客觀論斷或分析。我很納悶的是,他總是會用一種「品評歷史人物」的欣賞與包容,來對待他身邊那些仍在關係之中的人。乍看之下,他是很喜歡東聊西聊的人(特別喜歡聊看過的書),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他本人才是一個讓人聊到停不下來的主題。奇怪的是,以前有時候他人不在現場也可以成為話題焦點,現在他離開之後,我想就更難脫離被大家「聊」(可能性高於默默不語地懷念)的對象。
2010年我畢業搬離系館,接著,鴻昌也畢業了。我們各自開始了有家庭的中場人生,隨之而來的很多事情讓我們不再輕盈瀟灑,甚至失去了些許俐落。在我們相識的第二個十年裡,見面機會少了,但是,每次見面仍然像當年一樣有聊不完的話,直到旁邊的人都翻白眼,或者與家人的約已經遲到。我依稀記得,2018年底他決定轉身離開台灣社會學界,不再期待那些希望渺茫的求職時,仍然有著過去那種提得起放得下的氣度與包容。直到他突然的離開,我才發現,留下來的我們或許才是承受不起這個損失的一方。
很懷念,自己在社會學道路上的兩個十年,我們曾經開懷地聊過這麼多。我不敢期望未來會有機會遇到像他這樣的人,但至少,這段時光可以讓我跟其他人(認識他不認識他的都好)有聊不完的他的故事,其中有他的溫情、他的知識、他的樂觀,與他相處的種種歡樂的時光。
我大約是在2000年準備考研究所的那時開始認識鴻昌學長,之後因為我們都有著長時間待在系館研究室的生活型態,到2010年畢業為止,幾乎是很常見面。鴻昌是個很溫暖的人,對人的真誠不會因為你是(遜遜的)學生或是(知名的)學者,而有很大的落差,如果談論的話題跟知識有關的話,更是如此。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特質真的是很難得。
跟學長聊天談論社會學相關的東西(我不會想硬說這一定是在聊學術),總是有一種讓人很想繼續聊下去的感覺。碩士班畢業以前不太知道為什麼,到了博士班中後期,漸漸體會其中緣故。我想,或許跟他(從化工系)到社會系之前,已經修過許多社科院其他系(例如:經濟、政治、法律)的課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說,他很能跟我聊法律學與社會學之間的差別,這實在是很難得的事,特別是關於知識本身的內在特性,與浸淫(或熱愛)其中者所養成的性格形塑,或者是兩者之間的相互構成。有時候我們也會像玩角色扮演一樣,從法律學跳到經濟學跳到社會學,來討論對同一個事情的不同觀點與其展現,甚至是彼此之間的知識攻防。其中深刻處有嚴肅也有輕鬆,但並非戲謔如網路上流傳的那種N x M的偏見格子、一句話惹怒OO系、或者學科鄙視鏈等等。
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佩服他的地方,或許是他在綜合比較過不同的社會科學的觀點之後,才選擇了社會學這條道路的緣故。不像我(或大多數人)有時很難區別自己是否出於逃避其他,才轉而把社會學視為一根浮木,為了求生或秀異而緊緊抓住,卻事後貼上「一見鍾情」的標籤。他這種令人佩服的地方我當時不知道怎麼描述,後來看到一些比較炫的口號(例如「跨領域」或「科際整合」之類的東西)才瞭解大概可以這樣說。閱讀相關學科的知識,以此持續反思與社會學結緣的初衷,在很多人看來只是他的一種個人興趣。隨著歲月成為人生的沉重負擔,我才漸漸發現,這看似個人的事卻決定了一個社會學博士,能否坦然樂觀地面對殘酷現實的學術市場,甚至面對自己與社會學的關係。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廣博涉獵,一直都是他對知識保持好奇心的動力,讓他溫暖且恆續的光源,照亮像我這樣(有時虛無隨波或是自暴自棄)的人。
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的場景,是跟他在系館後門的販賣機附近,討論自己碩士論文初稿的一章又一章。他總能釐清我很多攪在一團的想法、刺激我想出新東西,甚至也能讀出偽裝艱澀文字背後我的自信不足。在研究所的學習過程中,我漸漸對這樣的關係上癮,喜歡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我的觀察、我讀了什麼書、寫了什麼報告。但我不會用「老師」來形容他,可能是這個符號已經被另外一類關係所佔據,兩者明顯不同。跟他有過比較深刻互動的學弟妹或許能瞭解我的意思。一時間我還找不到合適的文字去描述,但「學長」一詞只能扮演一個方便卻不精準的代號。因為他改寫了這兩個字過去給人的那種權威、恣意的性質,當然,「理論」、「歷史」、「讀書會」等詞彙也是。
在系館將近十年的朝夕相處中,我認識的鴻昌雖然樂觀,卻不是那種天真或有各種「不務實」症狀的人,更不會因為是以社會理論作為知識興趣,而對自己境遇或對外在環境產生過度烏托邦的幻想。與此相反,現實生活中的細細瑣瑣常常牽絆著他。
首先就是錢。他一直都在當課程助教與研究助理,但有意思的是,這既支撐了生活所需,也使其脫離了生活所需之累。拼湊幾個兼職工作的薪資以到足夠支撐生活開銷,但是,他卻把這些「工作」做到了一種「高於貨幣所得」的奇特境界。或許有人會笑他花太多時間(相對於薪資)在這些事上,他卻覺得自己已經提前攤還了許多未來要付出的「代價」。這種意義上的助學貸款我自己在剛教書的前幾年償還得很辛苦。在樂此不疲的同時,這些事竟然也從工作變成娛樂,達到開源之外的「節流」功能。我不覺得他在其中有任何的禁欲主義成分,也不相信他被困在自我剝削的虛假意識之中,但他確實使那些「為了生活所需」之事,成為幫自己脫離生活所需之累的助力。還記得當年面對後輩學弟妹對此問題的疑惑,他總是開開玩笑地說:「這是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喔!」我則在旁邊淺笑,心中OS:要學大概也很難吧?
再來是人情。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某種超乎禮物交換或人脈累積的「無所為而為」邏輯。一般來說,人際關係如果沒有利益或情愫在其中流動,很難長時間維持。可在鴻昌身上,我看到的多管閒事或好為人師(他自己的用語),似乎卻多了一種知識上的好奇。除了遙遠的人事物,我們也曾談論學生或老師,但是,他的好奇是一種具有同理心的長期觀察(也有時候被笑是種「溫情」),而非止於冷靜的客觀論斷或分析。我很納悶的是,他總是會用一種「品評歷史人物」的欣賞與包容,來對待他身邊那些仍在關係之中的人。乍看之下,他是很喜歡東聊西聊的人(特別喜歡聊看過的書),但我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他本人才是一個讓人聊到停不下來的主題。奇怪的是,以前有時候他人不在現場也可以成為話題焦點,現在他離開之後,我想就更難脫離被大家「聊」(可能性高於默默不語地懷念)的對象。
2010年我畢業搬離系館,接著,鴻昌也畢業了。我們各自開始了有家庭的中場人生,隨之而來的很多事情讓我們不再輕盈瀟灑,甚至失去了些許俐落。在我們相識的第二個十年裡,見面機會少了,但是,每次見面仍然像當年一樣有聊不完的話,直到旁邊的人都翻白眼,或者與家人的約已經遲到。我依稀記得,2018年底他決定轉身離開台灣社會學界,不再期待那些希望渺茫的求職時,仍然有著過去那種提得起放得下的氣度與包容。直到他突然的離開,我才發現,留下來的我們或許才是承受不起這個損失的一方。
很懷念,自己在社會學道路上的兩個十年,我們曾經開懷地聊過這麼多。我不敢期望未來會有機會遇到像他這樣的人,但至少,這段時光可以讓我跟其他人(認識他不認識他的都好)有聊不完的他的故事,其中有他的溫情、他的知識、他的樂觀,與他相處的種種歡樂的時光。